近日,中美在阿拉斯加的高層會談成為媒體和網絡熱議的重要新聞。
拋開兩國的政治糾紛而言,至少從幾個網絡報道的細節來看,美國政府(外交機構)很顯然沒有重視會談的細節對于影響會談的重要性。
細節的失誤或者說故意的疏漏,導致了儀式性的缺失,其預期結果就是大相徑庭。
以下失誤和觀察均來自網絡(如有不當之處,敬請見諒),但不影響本文的分析結論,即儀式對于政治會談的重要性。
首先看看哪幾個細節失誤:
第一是一場泡面引起的爭論成為網絡討論的一個熱點:
在第二場會談開始前的途中,記者聽到王毅問楊潔篪:“午飯吃了沒”,楊潔篪回應道:“嗯,我吃的泡面”。此次中美會談,美方作為東道主卻沒有為中國代表團安排午餐和晚餐,中國代表團只能自行解決吃飯問題。
第二是美方發言延時
美方作為東道主,在安排上自然要先致開場白;但是美方沒有按照原定的發言計劃進行,反而多次延時。在中美高層戰略對話這個場合上,所有的發言稿件都應該是精確計算,肯定是在規定時間內說完的。
其三是沒配同聲傳譯
據報道,中美高層戰略會談整體時間超出預計,持續2小時仍未結束。美方不僅在記筆記,還不斷傳遞小紙條,白宮的中國事務協調員精通中文,因此現場沒有同聲傳譯。單就翻譯這個問題上,美方此舉也是違背了外交基本禮儀的。就算這位白宮官員的中文再好,也難以與專業的翻譯人員比較,一旦在他翻譯的過程中出現錯誤,很容易造成政治誤判。

從現場視頻畫面來看,中方面前用于做會議重點記錄的,是整齊的A4紙;美方面前用于記錄的是參會人員隨身攜帶的大小不一的筆記本。在會議過程中,由于缺少統一的同聲傳譯,美方的參會人員甚至需要從筆記本上撕下一張作為傳遞信息的小紙條。
其四是美方工作人員染紫色頭發
鑒于這是一場非常敏感和重要的會議,美國的一位工作人員(可能是翻譯)染紫色的頭發,顯然如果不是故意的,就是不明白場合的重要性。

其他的細節就不再談論,比如桌布使用白色,顯然不適合政治會談的莊重性,桌間距如此之大,人為制造隔閡等等。
以上失誤或者故意而為顯然是不符合最起碼的外交禮儀和不重視外交儀式。
儀式性的缺乏,是本次會談的致命問題。
半個多世紀之前,美國法律學者、教授、耶魯大學法學院聯合創辦人兼美國上訴法院法官,羅斯福任命的司法部反壟斷司司長、新政資深人士瑟曼·阿諾德曾經睿智的說過一句話:“所有人類和機構的行為都是象征性的”。
瑟曼·阿諾德寫過兩本著作,《政府的象征性》(The Symbols of Government)和《資本主義的民間傳說》(The Folklore of Capitalism),其中,后者成為暢銷書。
儀式具有很強的象征性,任何機構的活動具有象征性,象征性支配著人們的行為。在政府活動之中尤其重要。
美國著名人類學家、人口學家、歷史學家、意大利研究專家,美國藝術與科學院(AAAC)院士,曾任美國社會科學歷史學會(SSHA)主席,布朗大學教務長的大衛·科澤的扛鼎之作《儀式、政治與權力》闡明了儀式在人類生活中的作用和政治生活的本質。本書對儀式這一人類學的核心議題與政治生活之間的關系進行了系統性研究,解釋了儀式為何一直都是政治生活的關鍵組成部分,指出無論是保守還是革命的政治群體,其成功都與儀式的有效使用息息相關。
大衛科澤的這本書由會展人讀書會創辦人王春雷老師在讀書會線下沙龍上曾結合儀式與活動的特質進行了系統性的分享,很有啟發意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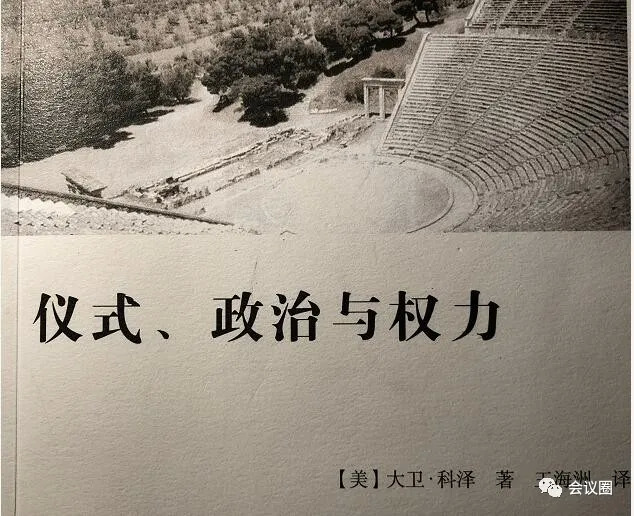
這本書的中文版序言之中,科澤教授的一段話我非常贊同:
“政治學家們通常不認為儀式在政治生活中發揮著關鍵性的作用。在美國政治學界,對物質利益發揮何種作用的研究占據著絕對的統治地位。事實上,所有的政治行為體都是象征的產物,從政黨到政府皆是如此,但這一點被忽視了:或是不予以承認,或是被認為無足輕重。我很高興從政治學者王海洲先生那得知,他的很多中國同行都認識到理解政治生活不可忽視象征維度的重要性。”
 (武契奇在白宮會見特朗普如同受審)
(武契奇在白宮會見特朗普如同受審)
 (武契奇與特朗普的簽約,用的是一張矮小的桌子)
(武契奇與特朗普的簽約,用的是一張矮小的桌子)
確實,科澤批評的美國政界忽視儀式性和政治性是普遍存在的,這也是美國政界在我國改革開放之初認為只要中國的經濟物質發展起來了就一定會走上美國價值觀的道路,結果事與愿違而找不到原因。其根本原因就是,中美文化基因不一樣,政治和儀式發揮著主導作用,而不是表象的經濟。
再回到會議之中的儀式,我國人民以及會議策劃者一直以來非常重視會議的儀式性作用。
小到一個席卡、站位,大到議程、發言排序都具有很深刻的象征性。
但凡連續多天的會議,東道主不可能不安排至少一次正式的宴請,無論以什么理由來規避一起吃飯這一環節都是失禮。宴請活動具有非常重要的聯系和加強紐帶的作用,早在原始部落時代就對于化干戈為玉帛起到很重要的象征性作用——人家部落在如此物質貧乏的條件下款待客人(甚至是敵意的雙方),本身就能夠起到化解糾紛的作用。很多不好說的話,在酒桌上以非正式的歡談笑語就可以化解。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是孔子的外交觀,不管出于什么目的,場面上的客套話和團結的話還是要講的,客套話不是虛假的奉承,而是一種對于彼此尊重的象征。
人都來了,談這么多不利于團結的引起兩國民眾厭惡的話,本身就是對本次和談的誠意不足。
最后,和談只是一種象征性,很多事情,其實在私底下就已經達成了。所謂的和談只不過是對媒體、對外界樹立一種形象而已,通過儀式性獲得合法權力。即便是橡皮圖章的會議,依然具有很強的儀式性的權力約束。
孔子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但孔子并沒有說己所欲施與人。這就是孔子的睿智和偉大之處。孔子的儒家文化協調的是人與人的關系,這是政治的核心,而儒家文化強調的禮儀正是儀式,這也進一步驗證了大衛科澤先生的政治觀點。
杜月笙曾經說過:“人生有三碗面最難吃,人面、場面和情面。”這三碗面正是象征性和儀式。
 微信公眾號:會獎CMIC
微信公眾號:會獎CMIC打開手機微信“掃一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