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多世紀以來,歐美日憑借工業化革命的成果,將整個世界撕裂成了兩半: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富國和窮國。就像窮人會仰慕富人一樣,窮國也會高看富國。什么時尚、潮流、品位等等,只跟“富”有關,要是“窮”的話,只有跟風的份兒。這實際上是一種正常的社會現象——前面的人領路,后面的人跟著學,時間長了,整個社會就跟著進步了。改革開放近四十年,就是中國向發達國家學習并與他們拉近距離的一個重要時間段。作為“學生”,我們的“成績”還不錯——有的時候還會有點飄飄然,但所有頭腦清醒的人都知道,我們之與發達國家,更多的時候還得繼續當“學生”。這就不難理解,為什么我國會議展覽業界,普遍都把“國際化”都成了一個努力的方向。
照理說,會議展覽業的“國際化”并沒有多少可以討論的東西——哪兒差,跟人家學就是了;要想讓他們購買我們的產品與服務、讓他們和我們一起開會,邀請他們就好了。可事情沒那么簡單,中國會議展覽的“國際化”總是與很多事情交織在一起,讓原本清晰的“國際化”線條變得難以辨認。
我們來看看中國會議展覽“國際化”的線索:
展覽活動與展覽業。對于展覽參與者而言,展覽活動就是一個交易或者交易支持的平臺,至于是否參與以及如何參與,他們判斷的標準很簡單——看看對業務拓展有多大幫助。沒人會關心一個展覽活動有多高的“國際化”參與率,他們只在乎有多少“買家”或“供應商”與自己有關。與會議相比,無論是全球還是中國,展覽活動更早進入平臺化、品牌化發展階段。所謂“平臺化”和“品牌化”,主要是指展覽活動與展覽參與者、展覽城市之間形成了一種相對穩定的合作關系。每個展覽活動因其所處的國家與城市的不同,因其在該行業、領域中所處的地位的差異,會擁有不同的參與者群體——其中就包含相應的“國際化率”。一個展覽會的“國際化率”并不全由組織方說了算,所在城市主觀努力能起的作用就更小。也就是說,一個展覽活動究竟能夠達到多高的“國際化率”,刻意的追求并沒有多少正面意義。
所謂“展覽業”,就是一個國家或者區域,把展覽活動以及由此引發的一系列經濟行為作為一個產業形態來考慮,并愿意通過長期的、系統化的努力來擴大它的社會經濟效果。一個城市是否有可能把展覽業發展成一個重要產業,跟很多因素有關,比如國家的經濟影響力、城市的體量、知名度與戰略定位、城市所具有的會展業所需的基本條件等。除此之外,展覽業還有一個“先來后到”的問題——一個行業或領域能夠承載的展覽活動數量是有限的,先到者就有更多的機會成為排他性的“品牌展會”;在基本條件相當的情況下,哪個城市率先發展展覽業,哪個城市就有更大的機會成為“展覽中心城市”。地球上并不需要太多“展覽之國”,一個國家也不需要那么多“展覽中心城市”。在全球、全國展覽業格局已經基本形成的情況下,任何一方想要想做出較大的改變,都是一件很難的事兒——包括國家、城市展覽業的“國際化”程度。
有人說,很多城市通過會展資金吸引了不少展會。沒錯,是有效果的,但這很難改變展覽業的基本格局——絕大多數“品牌展會”,一定會綜合考慮各種因素,不會因為少量扶持資金而輕易改變活動舉辦地。
國際展覽業幾十年的穩定發展,讓國際買家、國際展商變得更加成熟、理性。這樣一來,后起的展覽城市想要在短時間內通過單方面的努力,來改變國際買家和參展商長期形成的業務習慣,肯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指望國際知名展覽公司來幫你實現“國際化”的夢想,基本上也是靠不住的。它們到了中國,從某種程度上說已經變成了“本土公司”——中國展覽業的現行規則對它們更有實際意義。
會議與會議業。相對于展覽和展覽業,會議與會議業的“國際化”更是一項漫長而艱巨的任務。從理論上講,一個國家的市場規模越大、國內外影響力越高,它境內舉辦的展覽活動的“國際化”程度就應該越高。這是一種可以感覺得到的正比例關系。而會議與會議業的“國際化”就不太一樣——因為國際會議、國際獎勵旅游活動的組織者和參與者對于國際目的地的要求,“市場規模”只是一個不太重要的因素,除此之外至少還有十幾項,而其中任何一項都可能對其目的地選擇產生重要影響:語言、簽證制度、外事審批制度、國際會議申辦機制、協會管理模式、硬件設施水平、會獎專業服務、旅游服務、高端旅游產品與會獎產品等等。
我國有不少學術會議、行業會議辦得不錯,但“國際化”參與率卻一直上不去——語言就是一個重要的制約因素。美國協會類會議的國際參與率,可以達到5%-15%,就與其語言的國際通用性有關。再說國際會議——我國2016年接待的符合ICCA標準國際會議的總量,由2015年的333個增加到了410個,是多年來增幅最高的。但相對于中國龐大的經濟體量而言,這是一個很小的數字。410個會議,平均規模不到400人,參會者總量加起來也不超過20萬人——再分散到一二十個城市,就更不起眼了。靠這個數字來拉升會議目的地城市的“國際化率”,恐怕很多城市的愿望都要落空。
每年落地中國的國際會議基數低,實際上也不太要緊,只要手里握有可調控的手段,就能夠保證每年都有較高的增長率。可遺憾的是,根據這些年的觀察,國際會議的事情基本上是聽天由命——幾乎沒有什么有效的手段來增加或者減少。就說落地中國的國際會議的數量吧,幾乎沒有幾個人能夠解釋清楚,為什么2016年比上一年增長了百分之二三十。有可能到中國來舉辦國際會議的國際協會,有數萬家之多,沒有人可以準確說出可能到中國來的那1%究竟是誰。有的城市做了一些努力,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想要改變國際會議在國內城市分配的格局,挺難——至少它是一項長期而耐心的工作。從目前來看,在影響國際會議落地中國的主要因素當中,“規則性”因素排在最前面——缺乏有效的國際會議申辦激勵機制和積極的入境簽證制度。一方面來看,國際會議屬于“外事活動”,不能隨意舉辦,得進行“管理”;另一方面,國際會議的申辦首先是該行業、該領域自己的事情,它們內部的機制理不順,外圍的會議業再著急,也不會有太大的作用。
每年落地中國的國際獎勵旅游活動數量就更少了——可能只有國際會議數量的幾分之一,而且單個獎勵旅游活動的平均與會人數也比國際會議低得多。這些年做入境獎勵旅游的公司日子不好過,而且更不叫人開心的是,目前仍舊看不見黎明的曙光。這種現象有些叫人難以理解——中國社會經濟越來越進步,可為什么外國的獎勵旅游團不愿意來?向業界資深人士請教,所得答案不盡相同。但在我看來,最可能的解釋是,發達國家高端人群所需要的高品質體驗產品與服務,我們目前還不成體系。觀光旅游的主要目的是滿足好奇心,因此除了向上走——去更發達的國家和地區之外,還會向下走——去一些不如自己的國家和地區。獎勵旅游可不一樣——他們只為獲得極致的會獎旅游體驗——這些往往跟“落后”關系不大。
有兩個問題值得討論:
1、“國際化”,要表象還是內涵?
在會議上請幾個外國人做演講,進行中外文化的思想碰撞,比較容易做到;做一個冠以“國際”、“全球”名義的論壇和活動,加入一些國際行業組織、進行一些國際合作、制定一些國際化的發展目標,等等,也都不是很難實現。這些“國際化”的工作內容,也有很好的實際意義,至少讓我們有機會接觸國際上先進的東西。然而只有這些顯然是不夠的。“國際化”的根基在于內涵,而這又是一項長期而艱巨的工作。打牢“國際化”的根基,“國際化”的苗子才能越長越好看。所謂“根基”,就是給國際會議展覽參與者真正所需要的東西,包括硬件設施和軟件服務。有了這些基礎,“國際化”的會議展覽參與率,就有可能逐步往上升。
2、“國際化”的發力點在國際還是在國內?
如果我說“國際化”的主要勁頭要使在國內,肯定有人會說我“有失偏頗”,但實際情況就應該是這樣。
先說展覽。展覽“國際化”的核心指標是國際買家和國際展商,而對于絕大多數在中國舉辦的展覽活動而言,能夠滿足他們需要的基本條件主要在國內。很多人都想建一個真正的“國際化”平臺——我們搭臺,歐洲人、美國人、日本人以及其它很多外國人,都在那里自己唱戲。這實際上很難做到。更多的情況是,我們搭臺,我們唱戲,他們參與。國內人自己的戲唱不好,外國人根本就不會參與。臺上十分鐘,臺下十年功。練不好基本功,臺上的戲就很難唱好。
再說會議與獎勵旅游。從理論上講,中國發展這么快,成績這么突出,加上人文和自然資源也都有很大的差異性,有錢有品的外國人應該愿意來。之所以不來,有人認為原因在于信息不通暢,我看不全是——問題更多地出在我們內部。一來是,我們內部國際會議申辦的機制不理順,他們想來也沒用;二來是,我們內功沒練好,人家不愿意來,或者害怕來。一位美國專家說得好:人的劣根性之一,就是總愿意高估自己,而自己根本就意識不到。從全球范圍看,國際會議與獎勵旅游活動可以選擇的目的地有很多,差異性也很強,中國大陸充其量也只是他們占分量很小的選擇之一。結論是,在他們的感覺里,我們呈上的美餐,沒有我們自己想象的那么好。
給自己定一個“國際化”的目標是好事兒,說明我們有上進心,可真要把這件事兒做好,還需要做很多細致的工作。關鍵是,這些工作什么時候開始呢?如果說我們前期所做的工作是“國際化”的序幕的話,那么我們特別期待著“國際化”的正劇早些開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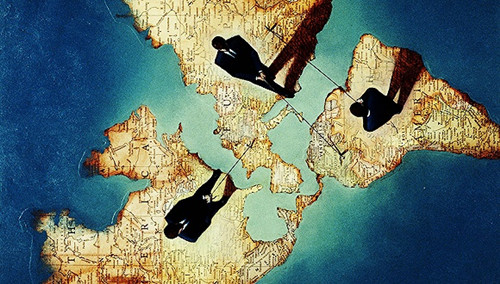
 微信公眾號:會獎CMIC
微信公眾號:會獎CMIC